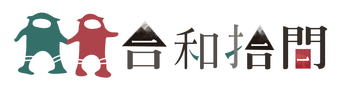|
-------------------------------------------------------------------
現在的我真的什麼都沒有,可是我很滿足,由內而外的滿足。單單純純的因為我活著能夠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所得到的滿足。原來要當人把一切不必要的都去除時,才有機會了解單單純純的存在是有多麼珍貴,我很想找到更適切的形容詞來形容,但是太難了,那就只是存在的感覺,有多少人知道存在的感覺是什麼呢?。 我像是完全清醒的做了一場最甜美安詳的夢。 第二部 真世界 啟程 「其實是睡得甜美安詳的你做了一個很清醒的夢」一個低沈的嗓音這樣說,因為許久沒聽到任何聲音,讓我的耳朵變得很敏感,也使那聲音聽來特別清晰,這讓我雖然看不到他,也能知道他就在我前方不遠處。 「我無意打斷你的思緒,但是我覺得還是早點讓你知道這點比較好。你休息夠了?還是要出發了?」 「我休息夠了。走吧」 「嗯…..」嗯,一個簡單的音節,卻包含著許多涵義,有些意外,有些嘉許,還有些理所當然。 我對自己異常平靜的反應也有些訝異,我以前曾經不只一次想像過這個重要的時刻,在我的想像之中我會很激動,或是有很多話想說,但是就在我聽到他說話的那一刻,我發現什麼都不需要多說了。我和他之間不需要更多東西,我不需要他慈祥溫柔的關懷,他也不需要我的崇敬感激的淚水,這些都是多餘的,他當然知道我是誰,而我也知道他是誰,這樣就夠了。 尾隨著光芒中的聲音,我和他一同前進,有時我們會說話,有時我們沉默。在沉默的時刻,我就憑著直覺走;畢竟看不見和聽不見並不會讓我錯失他,懷疑恐懼才會。 在路途上,我們斷斷續續的聊了許多事。 他說我對他們的了解其實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多,卻又比我以為的還要少了許多。如果我能夠拋掉那些已知的信念,再度去擁抱真實的話,那麼我就能夠就能喚醒那些隱藏於時間之外的記憶,而他之後會教我方法。 他還說,他們對每個人都有「計畫」,這套「計畫」無時無刻都在配合我們的選擇更動著,但是沒有任何的選擇會是在他們的「計畫」之外。雖然所有計畫的「目的」都相同,但每個人的時間和內容都是依個人的意願去選擇和決定的,他們會陪著每個人設定出個別的短期目標,也會適時的給我們一些建議。 在說這些話的時候,他並不只是在做例行性的簡介,而是一字一句的用它渾厚而細膩的嗓音去詮釋他所知悉的世界,他的口吻像是個經驗豐富的演說家,對於每個音節的拿捏都恰到好處,而他的用詞更是如同詩人一般精準且優美。 比如說他提到計畫時,他會用一種輕快而又充滿生命力的語調說:「計畫,不是對未來的想像,而是對未來的預見。想像只能給你一個畫面,預見卻讓你看見整個故事,但是千萬不要忘記你只能乘著想像的翅膀才能飛進未來的故事裡面。」 然而,若提到的是目的,他又會用一種截然不同的莊重語氣去解釋:「人們太容易曲解目的這個字的意思,一旦你把目的當做一個終點,你就會像追著尾巴的貓,永遠追不到它。目的不是死的,它是全宇宙最有生命力的事物,你要和它一起律動、歌唱、跳舞。」 他所提到的每件事都令人著迷,但也叫人迷惑,可是只要我臉上閃過一絲疑惑的表情,他就會停下來,然後再輕聲的安撫我:「你會明白的,一切都在計畫裡,只是現在還不是時候。」 在談話過程中,他有時也會問我一些我從來沒想過的問題,但卻都不告訴我答案,當他看到我搖頭晃腦的苦思時,就會開心的大笑,邊說:「很好,這下子你才會思考,一個好問題,就是能讓人思考的問題,你從思考中學到的,絕對會比你從答案中學到的還多。當你真正學會思考的藝術時,你就不會被問題和答案所困擾了。」 我有點不服氣,我覺得他會這樣說是因為他根本就是故意問我沒有答案的問題來刁難我;但他說要給我任何答案對他們來說是再簡單不過了,世間上所有的事情他們都有答案,但是這些答案往往不是我們能理解和接受的,所以說了還是等於沒說。「當你思考和理解力都不足時,我給你的答案都只會帶給你更多問題,但當你能把層次提昇時,不用我們告訴你,答案就會自己出現了。」 我還是無法完全同意他的論點,「但還是有些事情並不是層次提昇就能知道答案的啊,就拿名字來說吧,它就是一個必須要有標準答案的東西,雖然沒有人教我,但我很清楚人們只會記得住有名字的事物,名字就像是個約定,代表一種關係的認定,如果我們沒有了名字,我們就失去了身分。 就像我叫我的貓尼莫之後,牠就不再只是一隻路邊的流浪貓,而是我的貓;牠認得了自己的名字,也認得了我,而大家也認識了尼莫。所以像這些有功能性的事物,就必須有共同認定的特定答案,社會才能溝通和運作,如果都各說各話,用自己的答案和了解去詮釋,就會造成困擾和混亂,不是這樣嗎?」 「你不覺得你剛才已經給你自己答案了嗎?你還需要我的回答嗎?如果名字是為了功能性而存在,當語言沒有被發明時,名字就只是獨有的聲音或氣息或樣貌,人們藉由這些特徵去認識和記憶彼此,但有了名字之後,人們就不再把心思專注於真正直接去體會了解那個人。一隻狗可以憑嗅覺去記住它所接觸過的所有事物,但有了語言的人類,卻往往連自己媽媽的味道都記不得,那麼究竟是誰的文字和語言比較方便呢?名字又真的那麼重要嗎?」 「這是詭辯」我嘆了口氣,他的回答果然都會讓我產生沒完沒了的更多問題。「我們必須把事物命名才能增進意識的增長吧!就像我們現在溝通所用的每一個字句,也都是因為我們對於語彙有共同的認定,才能進行下去吧。」 「你回答的很好,我並不故意要刁難你,很多事,我們不輕易給你答案,只是要讓你們有機會自己領悟到新的事物,不過,既然你認同這點,為什麼還會從小就不喜歡人家給你的名字呢?」他反問。 「我不知道,我是本能的對於任何一個附加在我身上的特定名字感到莫名的排斥。雖然我還是接受了人們給我的代號,但心裡卻覺得不自在。」 「是不是就像當你認同了某一個你,就等於否定了其他的你。」 「對,就是這種感覺,就是有一種被切割開來的感覺。為什麼我會這樣呢?」 「我想這是因為妳還隱約記得自己曾經已許多其他不同的名字活在這個世上,使得你開始迷惑吧!」 他的話,等於間接的承認了輪迴的存在,也讓我對自己過去的身分產生好奇感,更產生另一個問題,如果人曾經以那麼多名字和身分活在世間,當他回到這個地方,到底要用哪一個名字好呢? 「你是我所見過對於名字這件事最執著的人了。」 「好像確實如此,名字對我來說就像是一個神奇的咒語以及最精簡的詩,取對了名字,事情似乎就會變得跟著順利,相反地,取錯了名字,就會讓事情完全走調。雖然莎士比亞說玫瑰即使不叫玫瑰,仍會依然芬芳,但我完全不認同這件事,怎麼可能一樣呢?每個字的讀音和含意給人的感受都是截然不同的,要從數萬的字詞中,拼湊出特定的幾個單字是多麼困難的事情啊!而且往往是一沿用可能就是幾百幾千年,如果幾千年前的人,把玫瑰叫做臭苞或是刺花,戀人們還會願意拿它來象徵愛情嗎?所以名字當然很重要囉。你有名字嗎?你願意告訴我你的名字嗎?」 「有何不可?我叫……..。」他的名字是一個我無法辨識的聲音;一個不屬於生物所能發出,反而像是源自於自然的聲音;有點像是風穿過林梢時的窸窣聲,又像是冰雪消融時,在冰層底下溪水再度流動的潺潺聲。 「很美的名字是吧!在每個人靈魂被創造出來時,都會被賦與一個很美的名字,獨一無二,專屬於你;這是在你靈魂深處不斷迴響的聲音,呼應你靈魂所擁有的特質。」 「那麼這個聲音究竟是什麼?一種神的語言?」 「是的,你形容的很好,神的語言,神的語言不是以文字在傳頌,而是一種稍縱即逝的感受,只有透過你與你的靈魂相呼應的時刻,你才能再度創造出相似的感受,並複誦這種語言。你記得剛才聽到我名字時有什麼感受嗎?」 「我覺得我好像身處於冰雪靄靄的北方國度,在冬春交際之時,冰雪開始消融,使得氣候更加寒冷,在那種時刻縱使有春風穿過林間,也會被誤認為是寒冷的北風。」 「還有呢?你還感受到什麼?」 「我還感受到在厚厚的冰層底下,有溪水流動的聲音,儘管那聲音如此微弱,但我知道那孱弱、細柔的小溪,終將用其頑強的生命力去溶解那巨大的冰層,使其能在春天時重獲新生。除此我好像還聽到一些騷動聲,是什麼呢?可能是在冬眠的動物,即將甦醒翻動身軀的聲音,也可能是草木要迸出新苗時,那蠢蠢欲動的聲音。」 「是的,那就是我的名字,這就是我從認識自己的靈魂後,就時時刻刻都聽到的聲音,也是我生生世世的名字。現在,既然你已經知道我的名字了,你可以用你能理解的任何方式來呼喊我,不論你用那一種語言來稱呼我,我都會知道你是在找我。」 「那我可以叫你「希望」嗎?」在我說這句話之前,我腦海中閃過許多詞彙,但沒有任何一個詞彙,比希望更貼近他此刻給我的感覺。 「當然,我很高興你喜歡我的名字,也很高興你想這麼叫我,我想再過不久,你也會找到自己真正的名字的。」我開心的點點頭,我相信那也會是一個很美的名字。 我們又繼續邊走邊聊了許久,然後他終於停了下來。 看著我們所停下來的地方,竟然仍是在一片光芒之內,什麼都沒改變,使得我不禁再度露出疑惑的神情,還好這次他主動告訴我答案了。 「不用懷疑,就是這裡。一個人真正想往目的前進的人,需要的不是身體的移動,而是意識的改變,改變你的意識,才能真正的前進。」 「那我們為什麼還要走那麼久。」 「走這段路只是讓你做好前進和改變的心裡準備,學習享受醞釀的過程是很重要的,何況世上從來沒有白走的路,難道你不覺得剛才我們的散步很愉快嗎?」 我點了點頭。 很難以置信,跟一個看不見的人經歷那麼長的一段沒有任何風景或娛樂的旅行,竟然會覺得如此愉快;難怪人家會說,旅行跟誰去比去哪更重要。 初見 「現在,我要用一點小伎倆,幫助你看見該看見的東西,這雖然是一個取巧的作法,但是如果運用得宜,總是會有很好的效果。就像佛像、十字架還有維他命一樣。」希望笑了一下,好像是對自己會說出這種話感到很好笑。然後又繼續接著說:「照著我說的做,我要你專心的凝視一個地方,目不轉睛的看著,好讓我把『意識眼鏡』傳送給你」 我聽著他的話,把目光停留在眼睛正前方約30公分的地方,並依照他的指示,不斷的想著意識眼鏡,但過了一陣子,還是什麼都沒看見。 「嗯……我想你大概是被「那個地方」搞得有點僵化了吧!沒關係,我們再試一次,這次我把意識眼鏡做成…...嗯……就跟你小學時的那隻眼鏡一模一樣好了,這樣你應該就拿得到了。」 我噗哧一笑,我當然知道他說的是哪一隻眼鏡。小學時我超喜歡粉紅色的東西,有一次看到一隻印著小花的粉紅色眼鏡,就苦苦哀求我媽買給我,至今我都還記得那眼鏡在櫥窗裡對我招手的模樣。 我照著他的指示又試了一次,果然這次眼鏡真的順利出現在我眼前了! 「在你把它戴上前,我們還有點小儀式要完成。」 希望要我用一種最誠懇慎重的口氣跟著他複誦:亙古不變的宇宙啊,我在此懇請您將您永存不滅的能量灌注於眼前的這隻眼鏡上,使我戴上這隻眼鏡後,能夠免除於自我的侷限,不再被幻象和妄念所蒙蔽,獲得宇宙的視野。我將再度看見花兒的芬芳、鳥兒的歌唱、戀人的心意還有我應當明白但我卻遺忘的一切。從此眼能看見心,心卻不受限於眼。 說完之後,我慎重的閉上眼,把眼鏡戴上,當再我張開眼時,我看見了。 眼前的他和我想像中的「他們」不太一樣,他長得比較像「我們」。 希望約莫是四十來歲,身長一米八左右,體格結實卻不會過於壯碩,有著深褐色的肌膚,和濃密的黑髮。剛硬的臉部線條,使他看來格外有個性,但也讓人覺得不好親近。我不清楚他的血統,但從他高挺的鼻子和東方的單眼皮來判斷,我猜測應該是中南美洲人和亞洲人的混血。 然而,若真說他看起來像人,感覺又哪裡不太對勁。他比我所見過的任何人都看來更精緻些,就連經過精心造型的名模,都無法擁有這種細緻感。該怎麼說呢,並不是說他長得特別好看,而是如果我們是在工廠生產的普通娃娃,他就是大師製作的手工限量版;他從頭到腳似乎都細膩的雕琢過,而且未受到任何的損傷和破壞。 就以皮膚來說吧,雖然是四十幾歲的人,但深褐色的肌膚卻完全看不到毛細孔,眼尾的皺紋不顯得老態,反倒像是為了讓自己看起來穩重些而刻意加上的裝飾。除此,他給人一種極其完美的協調感,彷彿他的眼神乃至於身上的每一條神經和肌肉甚至是毛髮,都能配合他的聲音和情緒,恰如其分的彼此支援著。 這讓我想起大學時戲劇課教授所說的話,一般人並不擅長使用自己的肌肉,一個好的演員必須不斷的鍛鍊肌肉控制的能力,才能得到各種戲劇化的表情和動作。而我眼前的這個人就像是個頂尖的演員,因為他的每個動作、聲音、表情都像是經過精心排練過後才會有的結果。 此外,希望的裝扮也讓我印象十分深刻。 他身穿一套亞麻材質的暗色西裝和純白的合身襯衫,脖子上圍著一條帶著暗紅花紋的淺紫色圍巾,腳上則是一雙造型典雅的棕色平跟船鞋;雖然是正式的服裝,但因線條十分流暢,加上他搭配得宜,看起來完全不覺得拘謹,而他微卷又有些散亂的黑髮,更增添了一種閑適瀟灑的感覺。我從來沒想過他們竟然會看起來那麼時尚。 看到我直盯著他瞧,他不禁又笑了:「你以為你看到什麼了。」 「你要告訴我你的外表只是幻象嗎?我覺得你好像假人一樣。」 「不,我的外表很真實,就是因為我的外表和我的內在是非常一致的,所以讓你看不習慣才覺得像假的一樣」 「所以你是一個很會打扮的混血兒?」我不禁有些失禮的脫口而出。 「不,這只是你現在所看到的外表。」 我被他用迷糊了,於是他花了很大一番唇舌,才讓我理解他的意思。 首先,希望告訴我並不是他特別的完美,其實人本來就應該長得像他這個樣子。我們之所以無法做到,是因為我們的內心和外在之間有許多的衝突、矛盾和壓抑,使得我們想笑的時候不敢笑,想哭又不能哭,明明心裡想去花園散步,卻逼自己坐在辦公室。久而久之我們的外表和內在的精神就開始分離,失調,我們的精神也開始生病,然後一切就變得不完美了。 「孩童絕不會犯這種錯誤,他們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能讓人感到很舒服自在。你能由他們的外表看到他們的內在:他們笑,你就會感到快樂,他們哭,你也跟著傷感,他們沒有想要運用自己的外表去控制別人,但身邊的人都會被他們感染和影響。你知道這是為什麼嗎?」 我搖了搖頭。 「因為真實才能擁有力量,這是宇宙不變的法則。當一個人開始不對自己內心誠實而試圖去戴上虛假的面具時,不論他的原因是什麼,他的靈與肉都會逐漸分離─身體會因為得不到靈的能量而開始生病;靈魂也會感覺要批著一張厚重的人皮過活是一件辛苦的事情。像這樣的人,就算他偽裝的再好,身旁的人一定還是會感受到的。」 希望這番話講得十分生動,讓我想到過去我遇到一些人,雖然滿臉笑容、舉止得體,但是在他們身邊不知不覺就是會覺得很拘束且不自在,而有些人,就像我在花蓮遇到的大叔,雖然長得沒特別好看,皮膚又黑,但是只要一想到他,我就會想到他那如同陽光般燦爛的笑臉。我想這大概就是因為我從他的身體,看到了他的靈吧! 「既然如此,為什麼你要裝扮得那麼花俏呢?我以為你們會崇尚質樸的樣貌呢?」我會說這話,是因為我印象中那些時尚圈的人,往往都膚淺又拜金的,擁有好看的外表卻心靈空虛,只會盲目追求流行,卻沒有自己的想法,所以我主觀的對於這種形象感到反感。 希望用一種嚴肅的表情看我,然後說:「你覺得美是一種罪惡嗎?」 我嚇了一跳,趕緊否認。 他跟我解釋,其實他可以化身成任何年齡和身分,也能自由的選擇各種打扮,但是他就是因為了解我,所以才刻意以這個樣貌出現,讓我能夠重新思考外表的問題。 「這可是我們最擅長做的事,我們懂得利用各種介面去跟你們溝通。我當然可以穿個袈裟或是白袍然後掛個光圈和翅膀之類的在你面前出現,但是你難道不覺得我為了讓你信服而刻意這樣做,也是一種偽裝嗎?穿什麼衣服並沒有什麼問題,有問題的是人們穿上衣服的心態。」 就在我還在思索他的話時,轉眼間他便換上了一套不同的服裝。 他的上身是一件色彩絢麗的編織直紋短衫,外罩華麗蓬鬆的黑褐色羽毛背心,下半身則是一件揉皮的合身長褲,在褲頭和褲腳都有縫上圖騰,腳上則是一雙草編的涼鞋,而頭髮也編成了髮束。 這套衣服,跟他先前所穿的風格截然不同,十分誇張華麗,但是穿在他身上卻不顯突兀,反而令人覺得高雅時髦。 「這是在距今一千七百多年前,我還是個南亞小島的石雕創作者時所穿的裝扮。可是即使是現在的你看來,不是仍舊覺得很「時尚」嗎?」提到時尚兩個字時,他刻意的加重了語氣。 「所以那是你在來到這裡之前在世間的身分嗎?」 「那只是其中之一,我就像你一樣,在世間輪迴了許多次才回到這裡。但你難道不明白嗎?輪迴幾次都不是重點,因為不論我在哪裡或以合種身分出現,我都會是個藝術家、創作者、詩人,這就是我的特質。我對美的喜好,不可能因為時代的改變而喪失,如果我有需要穿上服裝,就算只是用葉子來遮蔽身軀,我都能找到一片與我膚色最相襯的葉子來搭配,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在自然不過的事情。假如我今天為了讓人們覺得簡樸是美德,而刻意穿上醜陋粗糙的服裝,我就是在欺騙自己。 要記得,不論是你的身體也好,或是服裝也好,是你穿上了它,你有責任讓它跟你的內在一致,並讓你的內在透過它發光─你的身體和衣服和所有關於你的一切,都是你內在靈魂的延伸。 你可以沒有衣服,可以沒有身體,也可以喪失一切,但你不能沒有靈魂。一個有著美麗靈魂的人,不論如何都會看起來很美。相反地,一個喪失靈魂的人,不可能因為改變自己的外表,就能讓人看到美。沒有人會對美而感到厭惡,你所厭惡的是那種沒有靈魂的人,並不是美麗的衣服。服裝外表從來不是需要去費神擔心的事情,喜歡和討厭都是一樣的沒有必要。」 說著,他用手指了指我,叫我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原來他竟然在跟我說話之間,偷偷換掉我那邋塌的休閒服。 現在,我身上穿的是一件素雅的V領直紋小洋裝配上一雙綴有白色珠飾的柔軟平底鞋。 「你看,你不覺得這套衣服更像你嗎?」 然後他又像魔術師一樣,從空中抓了一個由白色雛菊和茉莉等所環繞出來的花圈掛在我的手上。我看了心裡開心的不得了,覺得這花串比任何鑽石珠寶都還好看,而且這套衣服不就像是我小時候塗鴉所畫的公主會有的裝扮嗎? 我明白了他要教我的不是人應該如何打扮,,他只要要讓我知道人應該要讓自己更像自己,讓自己由內到外都符合自己的特質,這才是一件真正「時尚」的事。 「等你認識了自己的靈魂後,我再送你一對白色翅膀,讓你更開心些」他俏皮的對我眨眨眼,「現在,我們別再耽擱了,想要完成你的書,你還有很多事要學習呢。」 「像是?」 「像是先去一個你一直很想去的地方。」 夢想成真 一顆顆晶瑩剔透水晶般的琉璃樹,連綿不絕的在我眼前展開,透明的樹體內滿載著閃爍著七彩光芒的能量,持續不斷的在枝葉間穿梭流動著,這使得樹充滿了生命力,每一棵都像擁有自己的靈魂和意識般,高唱著生命之歌。 「這是哪裡?」 「天堂」 他誇張的拉開雙手,並舉了個躬,就像是主持人掀開簾幕後所作的動作。我知道他這動作其實是在揶揄我當初一心想要到天堂而讓自己被困了那麼久。我有點難為情,就裝作不知情而若無其事的問他,「這跟我想像的很不一樣,為什麼我在這裡都沒看到其他人,他們都變成了這些樹嗎?」 希望搖了搖頭,帶著我走到其中一棵樹前,觀察了一會兒,便採下那棵樹上最大的果實遞給我。 「看清楚,你手上所握的是一顆成熟的『天堂』。我要你好好觀察這些『天堂』,直到你對它們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後,我才會再回來找你。在我離開的這段時間,如果你有什麼問題,你都可以問這裡的管理員」他指了指東方的樹林「他會告訴你關於天堂的一切。」 話說完,不讓我有任何問問題的機會,他就在我眼前消失。 我走進樹林中,不久就聽到一個童稚的歌聲,從樹林深處傳出。或許是由於地形的特殊或樹體構造和質材的特異,這整個樹林像是一個聲音傳送的通道,如同共鳴器般播送著那清亮的歌謠。 循著歌聲前進,走了約莫半個多鐘頭,我在其中一棵琉璃樹幹上找到歌聲的來源。那是一個有著一臉雀斑的紅髮小女孩,正一邊高歌,一邊將摘到的果實丟進樹下的琉璃簍筐,女孩一發現到我,馬上像隻無尾熊一般,以一種既緩慢笨拙,卻又熟練自在的行動,從樹上爬了下來。 她主動的走到我身邊,用肥肥短短的手來拉我,並露出她缺了門牙的笑臉來表示對我的歡迎。 她得意的跟我介紹她是這裡的管理員,對這裡的一切都很熟悉,什麼事都可以問她,我便問了 她剛才為什麼要那麼大聲的唱歌。 她回答:「我是在唱歌給這片「天堂」聽,這樣他們才會快快長大啊,我教你唱喔。」說著就扯開喉嚨,五音不全的唱道:「小就是大,大就是小;沒有小就沒有大,沒有大就不知曉。靜靜看,細細聽,小會變大,大會變小;你所要了解的事情就在那由小變大的過程之間,你所要找的結果就在那由大變小的瞬間。」 由於她的外表就跟一般幼稚園的小朋友沒有兩樣,看上去十分的天真無邪,讓我不禁想考考她知不知道這首歌的意思。 她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反而插起腰繼續認真的唱:「沒有大也沒有小,不見大也不見小;心中沒有分大小,眼中才見真大小。」。我馬上驚覺他唱這歌,是話中有話,所以趕忙為自己的不禮貌跟他道了個歉。 她踮起腳拍了拍我的背,假裝很老成的說:「不用擔心啦,我人看起來小,心眼可是一點也不小,這首歌是進入『天堂』的鑰匙,這樣你才能從天堂裡了解剛才那首歌的意思啊。」。 「是嗎?我還以為這裡就是天堂呢?」 「才不是哩」她噗哧大笑,好像我問了很蠢的問題。邊說話時,她像是在找什麼似的,抬著頭左顧右盼四處張望,好不容易鎖定了目標,就一溜煙的爬上樹摘了一顆比較小的「天堂」給我。 「我們先去參觀這裡好了。」 「怎麼去?」 「不是給你鑰匙了嗎。」 原來她沒在開玩笑,而是真的要用這首歌帶我進入天堂,就在我們兩個高唱著『鑰匙歌』的同時,我手上那顆「小天堂」迅速的朝四面八方擴展開來,我們也跟著不斷縮小,最後我和她就被完全的吸納進去「天堂」裡了。 這個「天堂」有著一個美麗的花園,風信子、蝴蝶蘭、水仙花、杜鵑、鳶尾花、番紅花,還有其他無數種我說不出名字的花卉和樹種把這裡點綴的色彩繽紛,宛如鋪上五彩的花毯,各色蝴蝶穿梭在花朵間,珍稀的鳥兒也在這處處可見。她撒嬌似的挨著我走,我們兩個沿著石板小徑走到一個巴洛克式建築風格的華麗城堡。 穿過迴廊走進堡內,數個僕役正有條不紊的細心擦拭著大廳的藝術品,有栩栩如生的石像,也有來自東方的貴重瓷器,就連腳踩的地板都有工匠在維護,而天花板的壁畫,也有藝匠拿著顏料在修補的。 「他們看不見我們嗎?」 「當然看不見了,人只能看見自己想看到的東西,我們對他們又不重要,他們當然看不見我們了。」 我和他在城堡中四處遊走,到處都能看見僕役在忙碌的做事,卻不見僕役之外的人。 「這個天堂美是美,但比我想像中辛苦許多,沒想到大家在天堂都是做這些事情啊。」 「那是因為你還沒看到這個天堂的主人,看到主人你就會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 我們邊欣賞城堡內的奇珍異寶邊尋找著主人,最後在經過第六個宴會廳時找到他。 雖然宴會廳裡有許多打扮華美隆重的人,但無疑的那個頭戴鑽石皇冠並且手拿黃金權杖的人才是我們要找的人。這個人身邊圍繞著許多絕世美女,這些美女彼此並不爭鋒吃醋而是一心一意的共同侍奉著他,他面露微笑似乎對這一切都非常滿意。 我們在城堡裡待了許多天,靜靜的觀察著他的作息。 他不做任何事,只是成天飲酒作樂。若想要有些餘興節目,他會跟好友去狩獵;在這裡每天都是適合打獵的晴天,而他也一定能夠滿載而歸。每隔幾天他會去看看住在城堡另一端的家人,他們總是對他的出現表現出非常欣喜的樣子,一家和樂:父母和藹慈祥,子女孝順友愛。可以這麼說,在這裡他要什麼有什麼,不會有任何事情需要他煩心和困擾。 「這就像是美夢成真一般嘛。」我欽羨的說。 「是啊,天堂就是實現人們生前所有願望的地方。」「真」(這是我後來知道她的「名字」之後,便決定這麼叫她了。)篤定的回答我。 就以這個天堂來說,它的主人,在身前是僕役,父母早逝,家境貧困,又長得其貌不揚,讓他一直很自卑,一生都是獨自一人;沒有什麼朋友,除了年少時曾跟鄰家的女孩有段若有似無的情誼之外,那女孩嫁人後,他也就未再受過任何女人的青睞。他的雇主是個生性嚴苛殘暴的人,對下人動輒打罵羞辱,讓他的生活更加無望。在他那乾漠般貧乏的生活中唯一的慰藉,就是在擦拭主人的貴重珠寶和藝術品時,自欺欺人的幻想那些都是屬於他的,唯有這樣想,才能讓他勉強在生活中找到一些意義。 「難怪這裡會有那麼多藝術品和奢侈品,也難怪他會想要成天跟美女在一起。不過天堂應該不需要僕役就能永遠保持美麗整齊吧!為何他的城堡裡要有那麼多僕役呢?」 「你不懂嗎?只有好人得到幸福還是不夠的,一定要看到壞人也得到懲罰和報應,人們才會覺得滿意嘛。現在你所看到那些僕人,就是他以前在城堡中所看到的賓客和富豪們,他討厭那些人,看到那些人那麼奢侈勢利,他卻那麼貧窮,讓他覺得很不公平,所以他就讓那些人都成了他的奴僕了。」 我能理解他的想法和心態,甚至相信對於許多人來說地獄的存在會比天堂的存在更重要,因為如果沒辦法看到自己痛恨的人下地獄,而讓那些人也進得了天堂,那麼天堂似乎就不是天堂了。 「那麼那些人當奴隸當了多久了呢?」 「你應該可以從他們的裝扮上猜得出來吧,他們已經在這邊快四百年了。」 「我的天啊,他們就這樣不斷的做事做了四百年,而他就每天飲酒作樂四百年。」我簡直不敢相信我所聽到的。 「四百年還好,並不算長,而且這裡原本也不是像你現在所看到的模樣,我還記得他剛來時簡直就像個暴君,每天不停的虐待那些奴隸,一段時間後才把注意力又轉移回美女和他的財富上。他目前所擁有的東西,是逐年不斷累積增加的。你現在所看到的城堡已經是他第十七個城堡,而他自己也是到了將近兩百多年前,才開始變得真正快樂起來,成了你現在所看到的樣子。」真晃動著她圓圓的小臉,搖頭晃腦的跟我介紹著,我感覺她似乎對每個天堂的歷史都熟悉無比。 「那他的快樂和平靜還真是得來不易啊。但那些奴僕怎麼辦,難道他們做了那麼多事,都無法贖罪嗎?」 「別擔心,天堂裡你所看到的東西,都不是真的存在,這裡只有他一個人,其他的都是他的想像而已。」 「就連他的父母和子女也是嗎?」我替這個天堂的主人感到不捨,因為他看起來是如此愛他的家人。 「行不通的,天堂是不能跟別人分享的,一個天堂往往是另一個人的地獄,若要讓每一個人的夢想都能夠實現,就非要一人一個天堂不可。」 「可是人家不是都說,在天堂可以看到自己生前所愛的人嗎?而且說不定真的有人能在同一個天堂相安無事的生活著啊」我沒說出口的是,我一直以為我會在天堂再看到尼莫。 「不行就是不行,如果這樣事情會變得很糟,一切都會變得一團亂。很不好,太不好了,這樣就真的會把每個天堂都變成像地獄一樣了。」真有些激動的說著「他們會留在天堂就是因為他們一定要必須一個人留在這裡嘛,否則他們根本就不用來啊。」 臉漲得紅通通的真,看起來更加可愛,使人完全無法嚴肅看待她所說的話。她看到我一副不是很在意的樣子,不禁更急切的碎念著:「不不不,妳不懂,妳不能想像如果真的那樣事情發生會變得多可怕。妳來的那個地方,人有很多限制,但是在這裡人的慾望卻可以無限的被滿足。」 「那有怎樣呢?如果一切都只是想像出來的,要多少有多少,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心裡其實也多少明白欲望的可怕,卻故意裝作毫不了解的逗弄著真,想聽聽她對欲望的看法。 「怎麼會沒關係呢?當然有關係啊!人的慾望絕對不可以無限制的擴張,誰都不行的啊,特別是還有其他人存在時,就行不通了嘛!」她來回的踱步走著,努力的想找出更好的說詞跟我解釋,但真並不像希望是個善於陳述的人,這讓她份外的難受,小小的眉頭也委屈的皺在一起,看得出來她真的非常想要讓我理解這點。 「走,走,走」她急切的拉著我的手「你自己看了就知道,我看過很多很多,所以我都知道。」 變調的夢想 從遠古到近代,從悲愴到歡悅,在一遍又一遍的鑰匙歌,我們參觀了許多不同類型的天堂。 真先是帶我去看了一個的少婦的天堂。那裏只有一個佔地不大的牧場和一間用樺木搭成的小木屋,加上一頭孱弱的母牛,幾隻雞和小小的菜圃,便是她在天堂裡全部的財產;然而少婦相當的安於現狀,並沒有奢求更多,因為在這裡她可以和她深愛的情人過著有如神仙眷屬般的生活。 少婦的情人對他體貼萬分,只要兩人在一起,他們的目光就不會離開彼此。他把她當做娃娃似的照顧:早上她還沒說渴,他就已經端上鮮奶給她;夜裡,只要她稍微翻翻身,他就會起來查看,擔心她睡不好。 無時無刻,少婦的臉上都露出甜美的笑容,那是只有熱戀中的女人才會有的幸福表情,不同的是,在天堂戀情並不會隨時間而消退。 「那個男子真的存在過嗎?」 「是啊,她生前身邊就是有著這樣一個情人,而且也真的對她如此體貼喔。」 我心想,如果有這麼一個完美的情人,我也會選擇這樣的天堂。 「你知道嗎,她情人的天堂跟她的也很像喔。」真拿給我另一顆大小和形狀都十分相近的「天堂」給我,「這就是他的天堂。」 真說的沒錯,少婦情人的天堂,幾乎是少婦自己天堂的翻版;一樣的木屋,一樣的牧場,想來那應該是他們生前共同的回憶。 然而在她情人的天堂中,卻有另外一個女性存在,那女性就是男子的母親。他們是三個人一同在木屋過著幸福的生活的。 「那少婦難道不能容忍母親的存在嗎?這樣她就可以在天堂和真正的情人相處,而不是和她想像中的情人相處了啊。」 「在世間的時候還可以,但是到了天堂她就不想在過這樣的生活,她無法忍受她母親老是剝奪她們兩人的相處時光,就算在天堂的時光是永恆的,她還是不想。」 「好吧!或許他們兩人之間還有一點問題在,但應該總找得到兩個能擁有一樣夢想,可以在天堂共渡生活的人吧!」 「是嗎?這是我看過最好的例子了。」 果然,真說的一點都沒錯。人的心是很小的,都無法容忍異己存在,我看過越多天堂,就越是肯定這點。 一個丈夫能為了實現妻子的夢想,而和妻子其他的情人在天堂裡和平共處嗎?一個孩子如果上了天堂之後,發現在天堂的父親或母親生活中還有其他子女,卻是他生前從來不知道的,他還會覺得那個天堂是他完整的家嗎? 撇開男女的感情糾葛,單純的親情,也難以在天堂實現。 就算在天堂人們可以隨心所欲的改變自己的年齡和外貌,父母和子女又該以何種面貌和身分相處?親子之間要回到哪一個時間點,才能得到最渴望的幸福?父母能夠接受完全成熟到不再需要他的子女嗎?還是她們真的喜歡孤單的留在家中,等待兒孫偶爾的來訪?那子女呢?如果一心想要跟父母相聚的子女,卻發現自己的父母也寧願在天堂扮演另一個孩子,依偎在自己祖父母的懷裡,那麼他又要去哪找可以依靠的父母呢? 每個人在世間上都是以多重身分活著,但卻希望在自己身邊的人,能夠依自己的意願在天堂以單一面貌呈現,這根本就是不可能達成的事情。就如同真所說的,如果不是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一個天堂,天堂就不再是天堂了,這裡將會和人間一樣充滿遺憾,夢想也就永遠不可能被實現了。 看到我沮喪的表情,真反而表現出蠻開心的樣子。 「就算你證明了你是對的,也不要露出這種得意的樣子嘛」我不禁想抱怨。 「才沒有呢!對的就對的,我本來就沒有想要證明什麼啊。我只是很開心你終於能看到一些真相。」 「這樣的真相,是很讓人難過和沮喪的。」 「你錯了!知道真相永遠是很棒的一件事。而且這些人並沒有受到任何傷害,相反地,天堂提供他們面對自己的一個很好的機會。」 真繞著我蹦蹦跳跳的打轉,誰能想到他如同孩童的外表和純真的舉動下,有著看穿一切的智慧,這個從沒降生到人世的小孩,用它小小的身軀守護著天堂,耐心的陪伴它們成長。 接著真帶我去參觀的是一批「宗教」天堂,在這類的天堂中,天堂的主人都受到宗教極大影響。 像是基督徒的天堂,絕對會有上帝和天使,他們喜歡像孩子一樣圍繞在上帝身邊撒嬌,反覆的聽著早已從聖經知道的故事和真理,並且以自己能進入天堂而感到自豪,相對的,這也發生在其他教派中,精靈、仙女、菩薩、和各種各類的神祇旁,都能看到渴慕的天堂主人。 他們用滿足祥和的表情告訴我,對他們來說只要能夠跟神待在一起,就別無所求了,這種反應我並不陌生,因為一直以來我對「他們」也是如此依賴;感染了宗教天堂所呈現出來的愉悅情緒和正向能量,我分外享受各種天堂主人想像出來的「神性」體驗: 神性,是在那聖潔莊嚴的殿堂裡徜徉漫步;是在沈靜清婉的樂音中追尋內心的平靜;是在恣肆的舞動身軀時,以狂喜的姿態讚頌神的偉大;是在見識到天堂的完美後,體會到自己的渺小。 「真,這些人的信仰如此虔誠,而且他們想要與神相處的要求並不過分,為何還是不能跟真正的神在一起?」表面上我說的是他們,其實我心中明白這也是我許久以來的疑問。 「真正的神?他們就是因為不了解真正的神,所以才要跟想像中的神在一起啊。難道妳到現在還覺得神應該是那個樣子嗎?他們還沒準備好面對真相,而妳也還沒看到真相。」真在說這些話時,表情顯得有些嚴肅,這是她之前都沒出現過的表情。 「真,妳的樣子好嚴肅喔,都不像妳了!」 「這樣子嗎?我想我大概是不知不覺中把自己當成老鳥了吧!」真吐了吐舌頭,繼續解釋「你不覺得你們很像躲在巢穴中,嗷嗷待哺,不肯學飛的小鳥嗎?」她邊說,邊縮起手肘做出小鳥學飛的滑稽動作,這會兒她又回復小孩的模樣了。 我聽懂了真的暗示,她說的很有道理,神不該是一台予取予求的販賣機,也不該是隨傳隨到、有求必應的侍者。許多自詡為聖者的人,在世上宣稱放棄一切,不為名利,事實上,在他們心中算盤打得比誰都精,他們的所作所為,不過是為了換得進入一個永遠不用付費也不會打烊的百貨公司和遊樂園的門票,以享用世間所買不到的夢幻逸品,並且被侍奉為上賓;所以一但到了天堂,他們所有貪婪的本性就全顯露出來了。 越是如此去解讀,就越讓我覺得事情很不對勁。 那些人(或許也包含我自己)眼裡看到的神,永遠是男的俊女的美,說話溫柔又善解人意,飛舞時令人目眩神迷,歌唱時讓人忘我陶醉,只要人有本事掏出大把信仰,天堂的眾神就任君挑選,滿足諸君的所有慾望,讓人簡直都分不清這是天堂還是酒家。如果有一天神變得又老又醜,既肥且髒,而天堂也只是老舊的雜貨店,他們還會願意拿信仰買單嗎?難怪他們只能和想像出來的神在一起。 然而,宗教信仰在天堂所帶來的也不見得都是愉悅的想像,反而也間接造就出許多「地獄」。會有這樣的情況,多半是因為那個天堂的主人認為自己生前所做的事會讓自己下地獄,所以創造各種殘忍不堪的刑罰來虐待自己,以滿足自己對地獄的認同感,有時甚至一困就是好幾千年。我就曾經看到一個和尚,在戰爭中為了自保而殺人,死後,他堅信自己一定會因此而下地獄,所以不論真如何幫助他,都無法讓篤信佛教的他,改善自己的處境。 「真,妳看到那麼多形形色色的「地獄」,不害怕嗎?」想到純潔如真,竟然時常都要面對這種景象,讓我心裡有點難受。 「不會啊」真一邊回答,一邊溫柔的拿起一顆晶瑩剔透的「地獄」在手中把玩。「妳看,這個妳認為很可怕的地獄,其實跟天堂也沒有兩樣,而且那些看起來好像困在地獄的人,有時還比較快成熟呢;反倒是其他的人還更容易讓自己陷入麻煩中,無法脫困。」 「麻煩?他們無憂無慮的還能有什麼麻煩,聽神說話,聽到膩嗎?」 「我剛才不是才告訴妳,麻煩就麻煩在無止盡的慾望啊。要找到成熟的天堂可不是那麼簡單的。」 於是真就帶我去那些完全被慾望蒙蔽的天堂,這類天堂的主人,已經沒有與其他人交際的需要,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自己身上,一個個全成了戀物癖、成癮症、自大狂。 成千上萬雙鞋、成千上萬部名車、成千上萬件珠寶、成千上萬樣堆積如山的物品,佔據了視野所及的所有範圍;即便如此,更多更多的東西還是源源不絕的湧入,淹沒了小小的天堂主人。 不論你走到天堂的哪一個角落,都還是能聽到他們大聲嚷嚷著:不夠、不夠、還是不夠,更多、更多、給我更多。 而耽溺於性愛、酒精或毒品的天堂主人也好不到哪裡去,由於擺脫了死亡的威脅,更多的性愛、毒品和酒精並沒要了他們的性命,反而是讓他們加倍瘋狂。交纏在一起的身軀,是心裡頭打不開的結;迷濛的雙眼裡,有著無法忘記的過去;插下的、飲下的、吞下的,是滿滿的空虛。他們不知道自己死了,也不知道自己在天堂,什麼都不在乎,一心只想繼續迷醉。 但更糟的就是那些自大狂了,他們創造出一堆假想敵,以不斷的征服和擊敗他人為樂。就算這些人並不知道我的存在,但他們那如鷹般銳利的眼神和充滿挑釁意味的氣息,也還是帶給我強大的壓迫感。我對他們的所作所為特別的不諒解;因為這些人明明就已經得到想要的一切,他們卻選擇要從別人痛苦落寞的神情中,來找到自己的偉大。 這些人都是世人眼中極為成功的佼佼者,甚至可說是天之驕子,他們卻沒有運用自己的力量來幫助他人,反倒倚財仗勢的掠奪更多資源。不論是在人世間,或是在天堂,所有的人事物對他們來說都只是一場遊戲,土地、金錢乃至於其他人的生命都只是遊戲的計算單位,是為了增添遊戲的趣味而存在;也是為了讓他們能在遊戲中贏得勝利而存在-任何無法為他們帶來好處的事物,就沒有存在的意義和必要。利益,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準則,也是唯一準則。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真的很難想像慾望可以摧殘人到這種地步,這已不是用病態兩個字就能夠形容,就像真說的,無止盡的慾望是很可怕的。 每多看一個天堂,我就越對天堂這個地方感到越反感,這裡彰顯了人性的自私、貪婪和醜陋,也強化了人的慾念。來到這裡的每個人幾乎都沾染上各種惡習,可以說到最後每個人都成了極端自我的瘋子。 「夠了!」當我看到又一個中東男子,「幻想著」自己有權要求別人以子女抵債,並在我面前,放肆的欺凌他的女兒時,我按奈不住的咆嘯起來。「不可以這樣子,天殺的,那只是個小女孩,不可以把那雙髒手放在她身上,不可以……..」即使我知道這一切都只是那個男子的想像,但我卻還是想要把那男人從女孩身上推開,只是我的每一拳都、每一腳都打在空氣中,那男人終究達到他的目的了。 我呆站在原地,久久不能釋懷,總覺得那男的也擊潰我了,他用惡行證明他能戰勝良知。真費了很大的力氣,才把我勸離那裡。 離開後,我只是低著頭不發一語,沒有心思再去參觀任何天堂,也不想跟真說話。真沒說什麼,兀自繼續做著工作:「觀察」這些天堂,是的,只是觀察卻什麼都不做。 我看著她掛著微笑在樹林間漫步,微笑著進出那些骯髒汙穢的天堂,微笑著看待我的無助,那麼的理所當然,彷彿她從來沒有懷疑過自己或是這個地方有什麼問題。 這讓我想對真發脾氣,我覺得她的工作讓他變得也很冷血無情,她怎麼可以眼睜睜看著那麼多可怕的事情發生在他眼前,卻無動於衷,她怎麼有辦法繼續用一幅如此純潔天真的面容出現在我眼前?她不應該這樣的,天堂也不應該是這樣,這是錯的,這一切都有問題。她難道不知道嗎? 我一口氣衝到真的跟前,把她手上的天堂搶走,並且怒視著她。這突如其來的動作,使真楞住了一下,但很快的她就回復平常的模樣,毫不驚恐也不害怕,只是安靜又柔順的站在我眼前,用那如琉璃般澄澈的琥珀色眼睛直望著我。 我質問她:「真,妳知不知道這些人所做的事情都是錯的!妳讓我感到害怕,你放任一切發生,甚至連嘗試去糾正他們的念頭都沒有,就讓他們得逞。」 「得逞?妳是指實現願望嗎?妳忘記了這就是天堂存在的目的啊!妳以前不是也一直很想到天堂嗎?為什麼現在又要因為天堂能夠實現人們的願望而生氣呢?」 我看著真那迷惑的表情,我已經無法分辨這是出於天真還是無知,或是她根本就是在裝傻。 「為什麼,妳竟然問我為什麼?」我氣憤的抓著她,「真,雖然妳不論是外表和天性都跟小孩一樣,但是妳在這裡應該有幾千年,甚至更久了吧!妳難道會不知道我為什麼生氣?」 真絲毫不害怕,只是皺起了眉頭。 「我以為妳會懂。」她輕輕的扭動著她的手想掙脫,但立刻她就知道這只是白費力氣,她墊起腳,企圖要用另外一隻手拿回我手上的「天堂」,我就把天堂舉得更高讓她勾不著,她嘆了口氣,放棄了嘗試。思索了一會兒,她才接著說。 「妳知道嗎?從來沒有人教我任何東西,沒有人告訴我甚麼是對或錯,但是我每天看,每天看,然後我就懂了,所以我以為妳如果跟我一樣一起看,妳就會明白我的感覺。」 「我不懂,我只知道這些是錯的,而且我沒有幾千幾萬年的時間,去做這些事,只為了理解妳到底在想甚麼。妳知道嗎?妳可以笑笑的看著這一切發生,而不感到難受,但是我看到這些卻是痛苦的,妳能明白嗎?」 我忍不住把她手掐得更緊,真因為疼痛而輕咬了一下唇,但除此以外,她並沒有再顯露出更多的情緒;顯然的,她並不是因為出於倔強而不哀求哭泣,即便是再不懂得察言觀色的人,都能看出來她的內心是一片平靜,絲毫沒有因為我的言行而起了任何波瀾。 「什麼是錯的?什麼是對的?是誰來決定?妳認為我可以決定嗎?還是妳想來決定?」 我洩氣的放開了真,我無法回答她,即使我心中有那麼一個想法,但我卻說不出口。 真見我一放手,便立刻如同小貓般輕巧的拿走了我手上的天堂,並從我身邊溜走。她拿著天堂走到一旁,一副很疼惜的模樣,一邊輕撫它,一邊把它拿到嘴邊小小聲的說著話。我猜不透她,那顆天堂並不會因為我的作為而受到傷害,也聽不到真說的話,她明明知道,為何還要這樣做? 於是我和真的僵持又回復了原狀,她繼續在樹林間穿梭,微笑的巡視著她珍愛的天堂,而且看似工作的更加起勁。她的歌聲和那如同謎語的歌謠不斷的迴盪在樹林間,也迴盪在我腦海裡。像是風聲、像是蛙叫、像是蟬鳴,像是這歌聲本就屬於這天堂的一部分,而我才是突兀的打亂這片祥和的唯一破壞者。 絕處逢生 真不再把她找到的天堂放在籮筐中,反而圍著我的四周放;東一堆,西一堆,毫無秩序可言的全被她拿來我身邊亂擺,她興高采烈的模樣,像是找到一個新的遊戲。她不時偷偷的瞄著我,孩子氣的以為這樣能重新引起我對天堂的興趣。 看到我沒反應,她就更加刻意的把幾顆特別大的天堂放在我的正前方,我乾脆閉上眼,賭氣的不看。當然,我沒忘記希望交代我的任務,只是我還沒準備好再去面對那些情景,也還不知道如何調適自己去跟真相處,我太脆弱了,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 看我閉上眼,真樂得乾脆把天堂都往我懷裡放,整個人也伏在我的背上,在我的耳邊大聲的唱歌,我用手把耳朵摀住,卻還是擋不住她歌聲的穿透力。 「夠了,別在胡鬧,不要逼我對妳發脾氣,我現在沒有心情陪妳玩遊戲。」我想制止真的胡鬧,真聽了不害怕,反而開心的笑了起來。 「妳為什麼要這麼生氣和痛苦呢?如果妳真的那麼不想要待在這裡,妳只要說妳不想玩了,妳只要說我放棄了,希望一定就會出現帶妳離開這裡。可是妳既不敢放棄,又不敢前進」 -- 是的,她說對了,我既不敢放棄,又不敢前進。
0 評論
發表回覆。 |
Site powered by Weebly. Managed by Porkbun